希拉克——“旧世界”的最后一个巨人
2019.09.27
来源 欧罗万象

撰稿人:宋迈克
2019年9月26日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五任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去世。现任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法国人失去了一位我们曾经爱戴、也同样爱我们的国家首脑。”并宣布9月30日为全国哀悼日,以纪念这位从政四十余年、历任第五共和最高职位的非凡政治家。
2005年9月,一向身体硬朗的希拉克首次因脑血管问题住院,从此,他便接连面对健康问题。2008年底,他装上了心脏起搏器;2011年,一份诊断报告显示他出现了阿兹海默病的前期症状。希拉克最后一次公共露面是2014年11月,那次他搭着保镖的肩膀,与时任总统的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一道进入会场。当时希拉克并没有发言,他虽然还面带微笑,但颤颤巍巍的姿态已经让人惋惜。2016年4月,女儿罗朗斯(Laurence Chirac)的去世又给了这位老人以沉重打击。这几年里曾多次看望希拉克的好友让-路易·德布雷(Jean-Louis Debré)曾形容说:“他的病情有点像一波上涨的潮水。有时会风平浪静,但它从不会退去。”如今,这位曾经身形矫健、以吃喝谈笑形象著称的总统也不能摆脱生老病死的规律,终于还是被这命运的潮水带走,走完了他86年的人生历程。

生平
青年“推土机”
半个世纪以来,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似乎是盛产法国总统的地方。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1969年至1974年担任总统)出生于康塔尔省(Cantal)。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74年至1981年担任总统)是在多姆山省(Puy-de-Dôme)第一次当选议员。后来成为左翼团结主导者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第一次当选议员也是在紧邻中央高原的涅夫勒省(Nièvre),那时他还是个中右派年轻政客,是出身于科雷兹省(Corrèze)的激进社会党(parti radical-socialiste)首脑柯耶(Henri Queuille)将他“空降”到当地的。而1932年11月29日在巴黎出生的希拉克的家庭正植根于柯耶所属的科雷兹省(Corrèze),他的父亲当时是银行职员,而他的祖父与外祖父都曾是当地的教师——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教师作为共和国理念的传播者,绝非等闲之辈。而后来的第二位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在1981年被派往科雷兹省参加议会选举,正是要去挑战当时已经是右翼领袖的希拉克。
这个现象中自然包含很多巧合,但这片至今仍充满乡土气息的地域或多或少地塑造了这些政治人物在国民心中的形象。在这个从来都向往自然、热爱乡土气息的国度,希拉克从科雷兹的乡村里得到的热情、开朗与对生活品味的热爱,都对他的个人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以柯耶为代表的那种避免公开纷争而寻求妥协的激进社会党传统似乎也在希拉克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着他从政的每一步。
在科雷兹省上了小学之后,希拉克来到巴黎地区念书,凡尔赛的奥什中学、巴黎的加诺中学,然后是路易大帝高中。1951年,他进入巴黎政治学院(IEP de Paris)读书,没有人会将那时的希拉克与后来的右翼领袖联系起来。那时的他曾在巴黎街头卖《人道报》(L’Humanité,法共刊物)。他的同学、后来的社会党总理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动员他加入社会党,当时还是共产主义青年的希拉克认为社会党过于右倾而拒绝。也是在巴黎政治学院期间,希拉克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贝尔纳黛特·朔德隆·德库尔塞勒(Bernadette Chodron de Courcel)。贝尔纳黛特出身名门,起初她家里并不喜欢这个来自科雷兹省的左翼青年,甚至拒绝在圣日耳曼街区的贵族们经常光顾的圣克洛狄德大教堂(Basilique Sainte-Clotilde)给他们举办婚礼,而是把这个女儿人生中的重要仪式放到了旁边的一个小礼拜堂中。贝尔纳黛特后来坦承自己原本的人生路线是要相夫教子,而丈夫的政治生涯改变了她的人生。


希拉克与夫人:1956年、2011年
3年后,希拉克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被国家行政学院(ENA)录取。1956年,希拉克主动请缨,前往阿尔及利亚服役。他表现出色,被授予中尉军衔。那时的他仍然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直到58年戴高乐将军(le général de Gaulle)重新出山后,才转入戴高乐主义(gaullisme)的行列中。1959年,他以第六名的成绩从国家行政学院毕业,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先后在国家审计院(Cour des comptes)、总理秘书处等任职,成为当时总理蓬皮杜的忠实支持者。60年代末,希拉克离开了高级公务员、幕僚这些岗位,投入了政治生涯。
1967年,希拉克还不到35岁。被蓬皮杜称为“推土机”的他在家乡科雷兹省的于塞勒(Ussel)成功当选议员。他的当选对当时的总统至关重要——487席的议会中,总统多数党派竟只得到了244席,以1席的优势勉强维持住了议会多数。希拉克的出色表现让他在选举后很快便被蓬皮杜召进政府,担任负责就业问题的国务秘书。作为当时政府中最年轻的角色,希拉克在一年之后的“五月风暴”里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作为政府的代表之一,参与了政府与各大工会在劳动部举行的谈判,促成了大幅提高工资、保障工会权利的《格勒奈尔协议》(Accords de Grenelle)的签署,为争取工会支持而试图化解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戴高乐在1969年因公投失利而辞职,蓬皮杜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二任总统。沙邦-戴尔马斯(Jacques Chaban-Delmas)出任总理,希拉克成为当时年轻的财政部长、中右翼政客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手下。1974年4月,蓬皮杜在任内去世,法国将在5月举行总统选举。被视为戴高乐主义“正统”继承人的总理沙邦-戴尔马斯很快宣布参选。然而当时已是内政部长希拉克却与一些议员和部长共43人一道,发布“43人号召”(« appel des 43 »),间接表达了对不来自戴高乐主义政党的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支持。这一转向之后,沙邦-戴尔马斯的民意支持度一路下滑,最终在第一轮中输给了吉斯卡尔·德斯坦。
在创造了第五共和国最高投票率(87.3%)的总统选举第二轮中,吉斯卡尔·德斯坦以第五共和历史上最微弱的优势(50.8%对49.2%)战胜了左翼候选人密特朗,而希拉克也凭借他在竞选期间的决定性作用而被任命为总理。作为戴高乐主义政党的代表人物,希拉克凭借对戴高乐主义候选人的第一次“背叛”,在41岁便成为了共和国总理,他和当时年仅48岁的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一道,为被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统治了16年的第五共和国带来了新鲜活力。
吉斯卡尔年代
出身贵族世家、对经济金融领域驾轻就熟的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以一副清新而睿智的面孔出现;而作为“推土机”,总理希拉克则充满能量和爆发力。两人分别代表着议会多数中的两派力量:中右翼和戴高乐主义者。来自中右翼的总统在经济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在社会议题上更加开放;而来自戴高乐主义政党“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UDR)的总理则更强调国家权威。就任头一年里,这届平均年龄只有52岁的新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举措:将选举年龄降至18岁、拆分广播电视总局(ORTF)、堕胎合法化……为了将法国建成一个“先进的自由社会”(« société libérale avancée »,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改革目标),希拉克作为政府总理,不遗余力地落实总统的改革举措。然而两人从性格到立场上的不合仍然逐渐扩大。总统过于自由化的主张让强调国家权威的总理愈发感到不适,总统在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不断安插自己党派要员也让希拉克渐生不满。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的“辉煌三十年”(« Les Trente Glorieuses »)在法国走向终结,面对高通货膨胀率和战后首次出现的经济衰退,中右翼的总统展开“冷却计划”,控制物价、收缩信贷,而戴高乐主义的总理则支持实施借贷,刺激经济。1975年下半年,希拉克的主张开始占上风,300亿法郎的刺激计划出台。工业产值开始回升,通胀率维持稳定,但贸易赤字自然开始大幅增长,法郎贬值,法国于76年3月退出欧共体的蛇形汇率机制(Serpent monétaire européen)。
身为总理同时,希拉克成功掌握了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控制。他在1974年底成为该党的首脑,并在次年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党内元老对这个年轻有力但时常不按套路出牌的总理不无保留,经受了“背叛”的沙邦-戴尔马斯说希拉克“只是在数议会席次的时候才发现了戴高乐主义”。无论如何,这时的希拉克已经扛起了戴高乐主义的旗帜,他越来越感到无法在一个中右翼总统的阴影下活动了。
1976年7月,希拉克向吉斯卡尔·德斯坦递交辞呈。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不具有我如今认为必须的手段来有效完成总理的职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决定结束(总理职务)。”总理主动辞职而不是由总统宣布解职,这在戴高乐和蓬皮杜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希拉克用违背戴高乐主义作风的方式,宣布了自己作为戴高乐主义继承人的独立,终结了与吉斯卡尔·德斯坦两年的合作。从此,两人在政治上从未再建立起信任。到2007年希拉克卸任总统、进入宪法委员会后,这两位前总统在宪法委员会中仍少不了互相揶揄。


希拉克和吉斯卡尔·德斯坦:1974年与2010年
辞去总理职务的希拉克开始全力投身政党活动。他在1976年底创立了“共和国联盟”(RPR),主张“法国式工党主义”(« travaillisme français »)。新成立的党派固然还属于议会多数,但希拉克对总统以及继任总理巴尔(Raymond Barre)的批判日益明显。他批判中右翼的自由主义政策是“野蛮的资本主义”,而将戴高乐主义宣传为是一种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
1977年,共和国联盟候选人希拉克成功战胜中右翼和左翼候选人,当选巴黎市长。这个新设立的重要职位(1871年到1977年之间,巴黎由国家通过总督直接管辖,没有市长)给了希拉克以全新的展示空间。他将之前国家计划的许多项目都重新规划:市中心大堂地区(Les Halles)的伞型设计(近几年被拆除重建)、左岸的快速车道等等,都是在他的主导下推翻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本意规划建设的。他还承诺净化塞纳河水质,目标是1995年可以在河中游泳。尽管这个目标没有按时达成(至今也还未真正实现),巴黎人还是在1983年和1989年两度选他连任。希拉克一直到1995年成为总统时才辞去巴黎市长职位,成为了历史上担任这一职位时间最长的人。


1980年,巴黎市长希拉克“逃票”跳过地铁闸机;1995年,当选总统后的希拉克在巴黎市政厅感谢支持者
在接下来1978年的国民议会选举和197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希拉克所领导的共和国联盟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党内也开始出现裂痕,主张进一步与总统党派接近的“吉斯卡尔派”和要求更明确地和政府切割的戴高乐主义元老们在路线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到了1981年总统选举前,面对党内已经表态参选的几名候选人,希拉克几经犹豫,还是决定以唯一能够“团结戴高乐主义者”的候选人的姿态,第一次投入了共和国最高职位的竞选中。48岁的他开始在全法国高密度巡回演讲,很快便在势头上压过党内主要对手、当时69岁的戴高乐将军的伙伴米歇尔•德布雷(Michel Debré)。他的竞选主张也从70年代末的“法国式工党主义”悄然发生了转变:他开始主张大规模减税、减少国家干预、对苏联更强硬的外交立场……在攻击左翼候选人的同时,他对中右翼总统的批评也同样激烈。
他在第一轮中获得了18%的选票,尽管落后于寻求连任的吉斯卡尔·德斯坦(28.3%)和左翼候选人密特朗(25.8%),没能进入第二轮,然而他的选民将对第二轮投票的走向产生关键影响。希拉克在第一轮投票后第二天号召选民“按照自己的意志投票”,而自己将仅以“个人名义”投票给现总统。在政党政治深入人心的年代里,作为仍属于总统多数党派的领袖,希拉克的号召竟如此不坚决,许多共和国联盟的支持者于是将此解读为希拉克对现总统支持有限。根据不少评论家的看法,这对密特朗在第二轮中战胜获胜吉斯卡尔·德斯坦(51.8%对48.2%)起到了关键作用。
两次左右共治
总统竞选的失利并不能阻止这颗政坛新星希拉克的上升。面对如今已经是前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希拉克逐渐确立了自己反对派领袖的地位。他继续着竞选时开启的右倾转向,从坚决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保持距离的传统戴高乐主义立场走向里根式的小政府、强硬外交的右翼主张。在接下来1982年省级选举、1983年市级选举中,共和国联盟接连取得好成绩。在党内元老之外,一批年轻人逐渐成长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公众注意。这之中便包括希拉克的得力助手阿兰·朱佩(Alain Juppé)以及当时最年轻的市长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希拉克本人也在1983年右翼成功赢下巴黎所有二十个区、实现“大满贯”后得以连任巴黎市长。
而执政的密特朗在这几年里则面临着接连的考验。在上台之初展开对工业、银行业的大规模国有化之后,面对糟糕的国际经济走向,政府的需求侧刺激并无效果,增加社会福利的政策花销巨大,通胀、财政赤字、失业率不断攀升……1981年10月起,法郎第一次贬值,到1983年3月,法郎第三次贬值,资本已经大规模外逃的时候,紧缩政策终于呼之欲出。在这次史称“紧缩转向”(« Tournant de la rigueur »)的大调头之后,密特朗的支持率一跌再跌。随着1986年议会选举的临近,右翼获得议会多数的可能日益加强。
在当时的制度下,每届总统的任期为7年,而每届议会的任期为5年。总统任期内的议会选举在1978年时就曾让吉斯卡尔·德斯坦面临困境,险些丢掉议会多数。而临近1986年时,民调的趋势更加显著:左翼在执政5年后输掉这次议会选举似乎已是必然。这给第五共和国带来了新的难题:一个总统权力至高无上的制度里,议会选举选出与总统政见相悖的多数时应该如何处理?对议会负责的政府首脑——总理是否可以由与总统政见相对的党派领袖担任?
在第五共和国缔造者戴高乐的视野中,“国家权力顶峰出现双首长(dyarchie)的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议会选举中总统失去了多数,表明他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但显然,密特朗并没有任何辞职的意向。共和国联盟内部对这一问题也不无争议,而作为戴高乐主义领袖的希拉克则坚定表示,如果议会选举右翼获得多数,他便应该成为总理,拒绝“双首长制”才会导致制度危机。
最终,1986年的议会选举中,共和国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UDF)构成的右翼-中右翼联盟以超过半数两席的优势获得多数,而其中席次更多的共和国联盟的首脑希拉克被任命为总理。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共治”(cohabitation)的情形:一名左翼总统和一名右翼总理共同领导国家。希拉克又一次以违背戴高乐本意的方式将戴高乐主义政党带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共治期间,总统根据宪法掌控着外交与国防方面的决定权,而总理则定夺内政方面的大政方针。密特朗与希拉克在一种互相敌视却又不无敬畏的氛围中共同完成了第一次左右共治的两年。
在此期间,希拉克政府延续之前的右倾经济主张,将密特朗执政期间被国有化的大部分企业再度私有化,并放宽劳动法规,增加解雇灵活性,取消了前政府建立的“巨富税”(Impôt sur les grandes fortunes)。伴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这些政策收到了一定成效,从经济增长到通胀率到失业率的各项数字上,法国经济都比此前有所好转。同时,在内政部长帕斯夸(Charles Pasqua)的主导下,政府出台一系列强力镇压手段打击犯罪,并收紧移民政策,大批遣返非法移民。帕斯夸的铁腕形象深受右翼乃至极右翼选民支持,却在向来强调平等博爱的法国社会激起了争议。而老练的密特朗也利用总统权限,拒绝签署右翼提出的部分民意支持度不高的法案,促使总理在议会几次强行通过法案,更进一步加深了民意的倦怠。左右共治期间,失去了一大部分权限的总统密特朗的民意支持率却不降反升。
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密特朗与希拉克进入第二轮,这场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对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在两人的电视辩论中,密特朗对希拉克一直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其为“总理先生”,以暗示自己才是总统,比对方身段更高。希拉克对此指出:“今晚我不是总理,您也不是共和国总统。我们是两个平等的候选人……所以请允许我称呼您密特朗先生。”密特朗则不动声色地回击道:“您说得很有道理,总理先生。”这段成为政治史上经典的对白在当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是政治动物,希拉克在当时的右翼阵营中已经可以呼风唤雨,但在老道的密特朗面前他却仍然略逊一筹。最终,密特朗以54%对46%的明显优势成功连任。可以说,希拉克通过两年的左右共治巩固了自己右翼领袖的地位,而密特朗则通过左右共治为自己的第二个七年总统任期铺平了道路。


密特朗与希拉克:1986年、1995年
二度参加总统选举失败以后,共和国联盟内部再次开始出现质疑希拉克的力量。由“正统派”戴高乐主义者帕斯夸和被归为“社会戴高乐主义”派(gaullisme social)的塞甘(Philippe Séguin)等人领导的派别从1989年到1992年间一直对希拉克的路线有所质疑,但都没能动摇这位前总理的领导地位。没有人怀疑希拉克会成为1995年总统选举右翼的候选人。而第二任期里的密特朗则无可挽回地再度面对着民意的丧失: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突破3百万……且左翼政客又接连陷入一桩桩腐败丑闻。到了1993年议会选举,右翼的共和国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获得压倒性多数,第二次左右共治开始。
希拉克将总理一职交给了第一次共治期间他手下的得力将领、经济部长巴拉迪尔(Édouard Balladur)。两人之间的协议十分明确:巴拉迪尔出任总理,而希拉克则直接瞄准了1995年的总统选举。然而1995年1月,民调支持率居高不下的巴拉迪尔不再遵循默契,宣布自己将参选总统,并将共和联盟的要员帕斯夸以及当时尚未年轻但已声名鹊起的预算部长萨科齐拉入麾下。对政坛上的倒戈与背叛早已不陌生的希拉克自然不甘示弱,随后也宣布成为候选人。虽然起初在民调中一直落后,但掌握着党的机器、政治经验远胜巴拉迪尔的希拉克最终实现逆转,在第一轮中压过了党内对手,与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Lionel Jospin)一道进入了第二轮。巴拉迪尔与希拉克的纷争留下的裂痕,给法国右翼留下了长久的影响。
登顶总统
在第二任期的最后时期里,密特朗清楚在自己的两届任期后,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已降至最低,他已无法希冀社会党内出现真正的继承人。希拉克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1994年8月底的一次仪式上,密特朗特地要求与他在巴黎市政府的办公室中单独面谈。其间,这位垂垂老矣、身患癌症的社会党总统对当时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的反对党领袖说:“轮到您了。您将当选。”相比后来的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密特朗似乎对这位来自另一阵营、却和自己有着更加近似的个人气质的右翼总理更有好感。
在1995年的竞选中,已是第三度参选的希拉克以“为了所有人的法国”(« La France pour tous »)为口号,主张弥合“社会断层”(« Fracture sociale »)。这一主题击中了目睹着社会分层加剧的法国民众的内心,而希拉克本人热情、饱满的亲民形象也与若斯潘始终理性、冷峻的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希拉克最终以52.6%的得票率获胜。驰骋政坛30年后、两度出任总理之后,这位63岁的科雷兹人最终登上了共和国权力的最高峰。
也许是对共治期间的经历记忆犹新,希拉克当选总统后选择了一种相对疏离的治国方式:他任命自己最为信任的年轻人朱佩为总理,自己着重于外交、国防方面,而将经济议题更多交付给总理担当。朱佩上任后,不仅继续着私有化的政策,还推出了被称为“朱佩计划”(plan Juppé)的关于退休、社会保险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朱佩计划的主要措施包括将国营领域的全额退休社会分摊金缴纳年限由37.5年延长至40年、建立年度社会保障预算法案以控制开销等等。这些旨在限制社会保障开销、减小财政赤字的措施引起了国营领域乃至全社会的强烈反对。1995年底爆发的大游行是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规模最大的。曾被希拉克盛赞为“我们之中最优秀的”(« le meilleur d’entre nous »)的朱佩一度态度强硬,要坚持改革到底。但到了95年底,铁路工人为首的大罢工开始:全国的铁路、巴黎的地铁线路几乎全部瘫痪,民意更多站在罢工者而不是政府一边,私营领域的员工、大学生、中学生等等社会群体也开始加入抗议队伍。在抗议活动的最高峰,全国大游行参与人数根据警方统计达到了100万人,而工会方的数字达到了220万。政府不得不做出退让:除了社会保障预算法案等部分措施得以保留外,关于退休制度等的重要举措则被撤下。
在法国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注定面临相当的阻力,然而1995年这样规模的反对浪潮,仍需放到当时的政治背景中理解:在竞选时高呼要弥合“社会裂痕”的候选人希拉克在当选总统后立刻便开始转向,称需要将重点放在减少赤字上,政府推出如此激进的紧缩方案,同时希拉克一直将朱佩推在最前线。这一直接而迅猛的转向让民意无法接受,激烈的反抗并不难理解。如同密特朗的支持率在1983年的“紧缩转向”后一落千丈一般,希拉克也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
到1997年4月,面对民意逐渐下跌的趋势,希拉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解散议会。1993年选举后的议会本应于1998年结束五年任期,而希拉克选择动用总统权力,提前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以寻求一个更支持他本人政策方向的议会多数。
第五共和国给了总统极大的决定权和操作空间,而解散议会就是总统最有威力的工具之一。历史上,戴高乐曾两次解散议会,并在随后的选举中重新赢得了多数。密特朗也曾在1981年和1988年两次当选总统后,解散了当时右翼占优的议会,获得了支持左翼执政的多数。而希拉克在1995年当选总统时决定不解散议会,因为1993年右翼大胜,希拉克认为当时的多数足以支持他主政。而到了1997年,面对同样一个右翼占据人数上绝对优势的议会,希拉克却决定将其解散。
今天看来,希拉克的用意也很清楚:再等一年,右翼的民意不出意外会继续下跌,不如趁根据民调还仍能取得多数的时候举行选举,并凭借获得的多数度过剩下5年的总统任期。但这一处在任期中间、没有出现大危机的情况下出于个人方便而解散议会的做法在当时遭到了反对党的批评,也在民意中造成了极大的不解。希拉克以为可以凭借这一出其不意的做法,让左翼无暇准备竞选。然而在若斯潘的领导下,来自社会党、共产党(PCF)、绿党(Les Verts)等不同派别的左翼政党在几个星期内便达成了竞选协定,以“多元左翼”(Gauche plurielle)为标签推出共同候选人。最终,“多元左翼”在希拉克宣布解散议会一个月后的选举中成功赢得多数,希拉克为巩固多数、重新加强合法性的政治举动彻底失败了。
在回忆录中,希拉克说,虽然当时的右翼政要大都支持他解散议会的决定,但他还是把自己视作这次失败的唯一责任人。不过历史无法重演,若斯潘在带领“多元左翼”赢得议会选举后成为了总理,第五共和国的第三次左右共治开始了。对于亲身经历了第一次共治时期的总理希拉克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只是如今他的角色变成了当年的密特朗。
在这次长达5年的共治时期中,左翼政府领导了重要的35小时工作制改革。在全球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法国经济也表现不凡,失业率有所下降。总理若斯潘的支持率一直很高,而总统希拉克则并无明显起色,势头时涨时落。在1997年议会选举失利后,塞甘被选为共和国联盟的主席,他任命1995年“背叛”希拉克而转投巴拉迪尔阵营的萨科齐为书记,标志着当年巴拉迪尔阵营的回归,希拉克在右翼阵营内部开始承受更多压力。1998年在法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上,法国队一路杀入决赛,并以3:0战胜卫冕冠军巴西队。在一片全国欢腾的气氛中,一直关注着比赛的希拉克的民意支持率也有所提升。而1999年,涉及共和国联盟诸多一线政治人物的一系列弊案开始被曝光,希拉克本人也牵涉其中,形象受到了很大打击。

希拉克、雅凯(Aimé Jacquet)、若斯潘在爱丽舍宫前共同举起大力神杯
2000年,在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总理若斯潘和推动下,希拉克接受了总统任期的改革:七年任期将改为五年,同时议会选举将在总统选举后很短时间内进行,以促进形成一个与总统一致的议会多数。他将这一第五共和最重要的制度改革之一交由法国民众公投决定,最终这一改革以明显优势通过。经历了几次左右共治的法国人最终决定改变制度以避免这一情况再度发生,而新制度的第一个试水者仍然将是希拉克本人。
第二任期
2002年的总统选举已经是希拉克的第四次总统选举了。经验丰富的他在最初民调并不占优的情况下,抓住减税和“不安全感”等几个议题,对左翼展开了有效的进攻。而社会党候选人、总理若斯潘则不得不面对“多元左翼”在竞选中分裂的现实:共产党、绿党等总统多数党派纷纷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极大地影响了他竞选的士气。在左翼极度分裂的背景下,2002年4月21日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带来了惊人的结果: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的候选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以16.9%的得票率超过了若斯潘的16.2%,进入第二轮,排名第一的希拉克也仅获得了19.9%的选票,创造了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轮胜者得票率的最低纪录。
左翼被淘汰而极右翼进入第二轮这一前所未有的状况令全国上下一片震惊。自1972年成立起,国民阵线这个极右翼政党渐渐从一个不起眼的边缘组织渐渐成为一个拥有全国知名度的政党,而它的首脑让-玛丽•勒庞从1974年开始便参加了几乎每届总统选举,1988年和1995年他都获得了大约15%的选票。然而在许多法国人眼中,国民阵线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与共和国价值观并不相容,而时常公开冒出种族主义言论的让-玛丽•勒庞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便更加难以接受。自1998年大区议会选举起,希拉克便主张实施“共和阵线”(« Front républicain »)策略:左翼和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联合,共同对抗国民阵线。而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后,他拒绝和勒庞进行电视辩论,表示“在不宽容与仇恨面前,不可能交易,不可能妥协,不可能辩论。”左翼政客也纷纷呼吁支持希拉克,拒绝极右翼。最终在第二轮投票中,希拉克以82.2%的绝对优势成功连任。
在这个五年任期的开始,希拉克任命中右翼的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为总理,开展了降低所得税率、部分放宽35小时工作时间限制、深化地方分权等一系列改革。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希拉克在外交层面的表现。“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展开“反恐战争”,法国支持了推翻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但希拉克坚决反对对伊拉克的入侵。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了一段著名的演讲,阐述了法国的反战立场,要求美国的行动必须得到安理会授权。这一坚定的反战立场得到了法国民意的大力支持,成为希拉克第二任期内最辉煌的时刻。
在国内政坛上,内政部长萨科齐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1995年希拉克当选后,支持巴拉迪尔的萨科齐遭到冷遇,2002年他东山再起、进入政府成为部长后,并不掩饰自己更大的野心。在2003年一次电视节目里,记者问他有没有在早上刮胡子时想到参选总统,他的回答是:“不止是在刮胡子的时候。”他与总统的矛盾从此日渐公开。2004年7月,在被记者问到与萨科齐的分歧时,希拉克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决定,他执行。”(« Je décide, il exécute。 »)
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希拉克所愿。2005年5月,法国民众在公投中否决了《欧洲立宪条约》,全力支持该条约的希拉克受到重大打击,拉法兰政府随即辞职。虽然萨科齐当时在民调中支持度更高,但希拉克还是选择了德维尔潘担任总理,而萨科齐再度成为内政部长、政府二号人物。2005年底,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市(Clichy-sous-Bois)爆发骚乱,骚乱很快就扩散到整个法兰西岛大区及法国全境,许多城市中出现了大量汽车和商铺被烧、示威者与警方激烈冲突的场面。这场持续了三个多星期的骚乱给法国带来了沉重的创伤,同时让作为内政部长的萨科齐的民意支持率又一次大幅攀升。在危机中,希拉克仍努力保持沉稳姿态,力求维护国家团结,而萨科齐则几乎在第一时间将矛头指向生活在郊区的青年移民,宣布无论是否合法移民,如果被判刑都应立即被驱逐出境。这些激烈的表态引起了政界的反弹,却进一步巩固了萨科齐强硬的国家秩序维护者的形象。


希拉克与萨科齐:1981年、2011年
而希拉克的民意则在2006年因为另一场运动而再度受挫:总理德维尔潘推动的“首次雇用合同”(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改革遭到了规模庞大的抗议,反对者认为这一初衷是促进年轻人就业的措施将会加剧年轻人不稳定的生活状态(précarité)。和1995年“朱佩计划”时一样,希拉克最终在庞大的反对声浪下让步,宣布修改该措施。
到2007年总统选举时,已经没有人能阻止萨科齐的步伐了。希拉克虽然厌恶这个与自己作对的部长,却也不得不出于党派立场宣布支持萨科齐。后者在5月初战胜了社会党候选人塞格莱纳·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当选为总统。希拉克在卸任前最后一次演讲中深情地说道:“亲爱的同胞们,没有一刻,我的心里、我的脑海不曾被你们占据,没有一分钟,我曾停下为这个非凡的法国而效力。我热爱这个法国,正如我热爱你们。这个法国因为她的青年而富有、因为她的历史与她的多元而强大,她渴望正义,渴望行动。请相信我,这个法国还会让世界震惊。”
遗产
“关于法国的某种理念”
现总统马克龙在纪念讲话中借用戴高乐的一个词组,称赞希拉克是“关于法国的某种理念”(« Une certaine idée de la France »)的化身。这一理念,用“人道主义”来概括可能最为合适。
希拉克的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他漫长政治生涯中在诸多社会议题上的立场。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期内,希拉克投票支持了允许女性堕胎的“韦伊法案”(« loi Veil »)。而在1981年密特朗执政时,他又一次与自己领导的党派中多数成员相反,投票支持了密特朗的竞选承诺之一——废除死刑法案。在2007年,希拉克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推动修宪,将废除死刑写入宪法。
1995年,希拉克在冬赛场自行车场讲话(discours du Vel d‘Hiv)中,首次承认二战中法国在大规模搜捕犹太人上的罪行。战后50年间,法国历届政府都拒绝承认维希政府为法国的合法代表,因而不承认法国的罪责。而希拉克是第一个勇敢地说出纳粹的罪行得到了“法国人和法国政府的帮助”的总统。“承认过去的错误、国家犯下的错误,绝不掩盖我们历史上阴暗的时刻,这只是在捍卫关于人类及其自由与尊严的观念。”希拉克开启的这一承认二战历史阴暗面的立场也在之后几任总统身上得以延续。
在政治层面,希拉克的人道主义体现为重视国家团结,避免制造对立。这一态度不仅落实为他在2000年前后开始一直坚持的“共和阵线”竞选策略,更体现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的整体作风中。曾把弥合“社会断层”作为竞选口号的希拉克从未像同一阵营的另一些政治人物那样,凭借激烈言语抢占头版,制造对立以吸引选票。在2005年的郊区骚乱发生后,内政部长萨科齐将骚乱分子称为“流氓”,称要用“强力吸尘器器清理”(nettoyer au Kärcher)郊区,而总统希拉克则在讲话中采用了沉稳的语调,指出这是一场“意义的危机、坐标的危机、身份的危机”。这种重视团结的“国民之父”的形象,与他的继任者萨科齐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与他的前任密特朗形成了某种一致。希拉克在密特朗逝世时发表的动情演讲中,出人意料地对密特朗这个“个人”表达了高度的欣赏,称在密特朗身上看到了“在意志支持下的勇气的力量”“把人放在一切计划的核心地位的必要性”。而如今马克龙也在悼念希拉克的电视演讲中动用了极为个人的情感,从遣词造句到镜头运用,都不难分辨出他试图重建这种总统之间超乎党派乃至近乎神秘的连结的意图。
在国际舞台上,“关于法国的某种理念”在希拉克身上体现为对法国独立外交以及对多边主义的坚持。相比他之后的两任总统萨科齐与奥朗德在外交政策上显著的亲美倾向,希拉克敢于同美国叫板、坚定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姿态一直为法国人津津乐道。半个世纪前的1950年,青年希拉克就曾在一些亲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反核号召《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便将这一宣言称为苏联的“宣传伎俩”。的确,在当时由德国、俄罗斯等国组成的西方反对伊战的阵营中,希拉克当时无疑扮演了领军人物的角色。
然而希拉克的这一坚定立场,恐怕不只是出于单纯的反美倾向,而是与法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独特联系相关。早在1996年希拉克访问以耶路撒冷时,他就曾对负责护卫他的以色列士兵发火,指责他们隔开行人的做法过于激烈。他混杂着法语和英语喊道 “这是挑衅,请你们停下”的镜头,很快在阿拉伯世界中传开,为法国赢得了不少支持。法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这种独特联系之中固然不乏殖民色彩,远非光鲜亮丽——希拉克本人在2003年访问突尼斯时,甚至曾在一位反对派人士绝食期间表态称“首要的人权就是要吃得上饭”,本·阿里后来的下场足以佐证这一表态的愚蠢——但面对如今中东的现状,希拉克在伊战时的做法无疑是站对了边。
亲民形象
希拉克让法国民众怀念的,除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高光时刻之外,更多的还是他和蔼的亲民形象。尽管希拉克和大量法国政治人物一样,经历了巴黎政治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的标准精英培养轨迹,但他却始终保持着远超其他政治人物的亲近群众的能力,也从未丢掉对乡土的热爱。希拉克既能与农民打成一片,又能与大企业主称兄道弟,既能走进工厂与工人握手,又能与艺术家高谈阔论的交往能力,在法国政坛可以说是无出其右。
最能体现希拉克在人群中左右逢源的能力的,就是每年的巴黎农业展了。从1972年担任农业部长起,希拉克便与这一展览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时起一直到他卸任总统后的2011年,他几乎没有漏掉一次农业展。左手一杯苹果酒,右手一块奶酪,希拉克不拒绝农户为他送上的任何土特产。他热情且自如的表现,让他成为了每年访问巴黎农业展的众多政客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在2005年,他甚至面对参展的奶牛夸赞道:“这些不是牛,而是艺术品!”


希拉克与农业展上的奶牛:1975年、2005年
这样一位不拘小节的政治人物,自然免不了成为各种政治讽刺的对象。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恶搞政治人物著称的讽刺节目“新闻木偶”(Les Guignols de l’info)中,希拉克的木偶绝对是人气最高的一个。尽管在节目中,希拉克木偶的话语时常荒诞不经甚至粗俗不堪,但它的那种搞笑的loser形象似乎拉近了木偶背后的真实政治人物与观众的心理距离。甚至有人认为,1995年希拉克能够反超巴拉迪尔进入第二轮并最终当选,“新闻木偶”节目发挥了正面作用!无论如何,在希拉克卸任总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木偶仍是节目的常客,不时跳出对时下的政治事件发表或是辛辣或是荒诞的评论,足以表明他的形象深入人心。

希拉克木偶的形象
在希拉克卸任之后,他的这种亲民形象随着他继任者萨科齐的负面表现而更加凸显。萨科齐胜选当晚在香榭丽舍大道的高级餐厅富凯(Les Fouquet’s)宴请各路名流:那个与农民一起享受土特产的总统不再了,新来的是一位“富人总统”。与希拉克可以在人群中如鱼得水相反,萨科齐则因为时常出言不逊而备受诟病,甚至还曾对一名抗议他的人公开喊道:“滚蛋,傻X!”( « Casse-toi, pauvre con。 »)所有这些对比,让卸任后的希拉克反而更加受欢迎。
变换的立场
如果人道主义情怀可以算是希拉克身上不变的元素,那么在其余许多方面,希拉克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向来不缺少立场转向乃至自相矛盾。
在经济议题上,希拉克可以说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一贯政策方针。面对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希拉克批判政府过度放任,要搞“法国式工党主义”;而到了80年代,面对左翼总统密特朗,希拉克俨然成了法国的里根。1995年以弥补“社会断层”为口号当选总统后,希拉克却开始强调控制公共开支以顺应未来的欧洲货币一体化,当朱佩计划激起强烈反弹时又决定收手;而2006年“首次雇用合同”从出台到撤回也只经历了3个月。他在总统任期内的数次退让,给人软弱不作为的印象。除了寻求妥协避免对峙的政治风格之外,真正导致希拉克这种不作为的,恐怕正是他经济思想的匮乏。
在欧洲议题上,90年代以后的希拉克无疑算是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1992年,他顶住来自塞甘、帕斯夸等人的党内异议,表态支持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aité de Maastricht),与当时的社会党总统密特朗在这一问题上站在了同一边。这一条约在当年的公投中仅以51%获得通过,希拉克的表态可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到了2005年,《欧洲立宪条约》公投时,他仍然以如果否决条约可能就会搞垮欧洲这样的主线为支持方造势,却未能阻止法国民众最终否决该条约,成为他任期内最重要的失败之一。然而希拉克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却并非一直存在:1978年,在几个幕僚的推动下,希拉克发表了著名的“柯山呼吁”(appel de Cochin),在这个明显是想效仿戴高乐号召法国人民抵抗入侵者的6月18日呼吁的宣言中,这位未来的法国总统称“欧洲联邦”的主张是“为美国利益所主导”,共同市场将给法国人带来“经济奴役、衰退与失业”,他甚至称支持一体化的法国民主联盟——也即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政党——为“外国人政党”(« parti de l’étranger »)。如此激烈的言辞,并未能给希拉克和他新创立的共和国联盟带来收益:在1979年第一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民主联盟在法国得票27.6%,排在首位,而共和国联盟的得票率仅为16.3%,排在第四。应该说,希拉克对欧洲问题的认识,可能并没有卓越远见。他从一个捍卫法国独立主权的“正统”戴高乐主义者渐渐变成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更多是随着一体化进程而接受了一体化的必要性,并在选举现实中做出了适时的选择。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总统任期的五年制改革。这是希拉克总统任内为人铭记的重要改革之一,然而对这项早在蓬皮杜时期就已提出、密特朗时期得到更多受众的改革,希拉克几乎是到最后一刻才终于接受。经历了密特朗的两个七年任期后,民意普遍认为七年时间太长,第二任期后期的密特朗垂垂老矣的姿态、他向公众隐瞒的癌症病情,都让五年制改革成为了当时的大势所趋。而希拉克作为当时的总统,还想寻求连任,并不想让自己将来的任期缩短。直到民意的趋势实在明显,为了不显得自己相比对手实在落后于时代,希拉克才在2000年终于将这一改革付诸公投。尽管投票率不高,但73%的支持率让五年任期制毫无悬念地通过。而希拉克本人在第二任期后期出现的健康问题,可以说再次印证了这一改革的明智……
据说在1995年竞选过程中,希拉克曾向一名亲信宣称:“我的煽动本领会让你们吃惊。”(« Je vous surprendrai par ma démagogie »)应该说,希拉克在这方面的能力并不只在90年代才体现出来。成为“共和阵线”的提倡者、抵御勒庞的“堤坝”之前,80年代的希拉克对待极右翼则是另一番姿态。1983年在德勒(Dreux)市的一次地方选举中,右翼的共和国联盟首次与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结盟。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作为共和国联盟主席的希拉克宣称,相比四名共产党人成为部长,几个国民阵线成员进入德勒市议会根本无足轻重。而1991年,希拉克本人在共和国联盟的一次活动中更是直接嘲讽外国移民带来的“噪音和气味”(le bruit et l‘odeur),他因此而一度被贴上“法西斯分子希拉克”(facho Chirac)的标签。在2002年总统选举第二轮之前,希拉克着实花了一些年份才基本洗去这一名声。

2002年总统选举第一轮结果出炉的一刻
弊案
在希拉克担任共和国联盟主席以及巴黎市长的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围绕巴黎及其周边由共和国联盟执政的市镇而形成了一张广阔的人事关系网络。在这个庞大的网络的掩护之下,一些政治操作走过了法律边缘,许多政商关系也向灰色地带发展。由此牵出的诸多弊案在90年代至今逐渐被揭发、调查,不仅打击了右翼政党本身,让希拉克的形象大打折扣,也加深了民众对政治的普遍不信任。
在希拉克的总统任期内,关于“巴黎廉租房案”(Affaire des HLM de Paris)的进展就给希拉克的民意支持率带来极大打击。这一案件尽管最终没有将共和国联盟的政治人物判罪,但法官明确指出了“有各种事实证据支持的大量证言表明”,共和国联盟内有人曾试图通过廉租房的建造商那里获取资金,以“资助该党政治活动”。
这些弊案中,“巴黎市政府虚假公职案”(Affaire des emplois fictifs de la mairie de Paris)成了最终让希拉克本人被判罪的案件。在1986年到1996年的时间里,巴黎市政府虚设公职,为20多名实际上是共和国联盟的雇员发工资,总金额高达数百万法郎。2004年,先是当时已回到波尔多担任市长的前总理朱佩被判有罪,还在总统任期内的希拉克一直处在总统豁免权之中。而2011年底,希拉克终于没能逃过法律的判决:巴黎轻罪法庭(tribunal correctionnel de Paris)以“挪用公款”和“滥用信任”(« détournement de fonds publics » et d’« abus de confiance »)判处希拉克两年缓刑。对当时的共和国联盟乃至其他政党——社会党在90年代末也曾有一系列丑闻,一位前第一书记也曾因虚设公职被判罪——来说,通过虚设公职乃至公共市场的献金方式来支持政党活动,是一个当时尽人皆知的行为,都是为了政党运作,其中并没有太多个人的得利。但法官终究没有放过这些按潜规则操作的政治人物,一直追责到了前总统。虽然年事已高,希拉克因身体原因未出席在判决现场,但前总统被判罪在第五共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审判在全国引起的巨大震动。
身后
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与问鼎总统的经历中,希拉克给法国右翼留下了深远的人事遗产:当今法国政坛的许多右翼主要人物都是希拉克时代成长起来的,甚至与希拉克本人有着直接联系。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少有人能分辨出“希拉克主义”(chiraquisme)的内涵。在这位承载着整个一部戴高乐身后的第五共和政治史的总统身上,却充满着第三共和时期激进社会党人的气质。除了强调国民团结抚平社会断层、拒斥国民阵线、捍卫世俗性、坚持法国独立外交等这些的确意义重大的价值立场外,希拉克在整个政治生涯中并未体现出在社会经济乃至国家制度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希拉克主义”实际上既不属于激进社会党人,也远离了戴高乐主义,而更像是一部分戴高乐主义的价值观与一种激进社会党人式的政治实践的混合体。相比戴高乐主义给法国留下的丰富思想资源,“希拉克主义”同“密特朗主义”(mitterrandisme)一样,是对一位书写了法国历史的政治人物一生的概括,但难以构成一致的价值系统或政策导向,并将随着他们主人的逝去而仅停留在政治史家的辞藻之中。
同时随着希拉克远去的还有第五共和国总统高大乃至神圣的身份和一种属于上个世纪的从政方式。这种身份下的共和国总统虽然有明确的左右归属,却同时是国民团结的担保人,拥有道德权威和较高民意支持,集中掌握着重大乃至过度的权力。这种从政方式下,政治人物的政策主张和性格气质在民意中几乎同等重要,他们的公众话语尽管有时不能兑现却还尚未大面积贬值,他们的暗箱操作乃至腐败也仍有很大空间。随着媒介的迅速发展、信息日益走向即时而琐碎,这种“国民之父”的总统形象变得不再现实。希拉克卸任后的10年里,他的一右一左两位继任者都先后成为了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超级总统”萨科齐大包大揽、行事专断、制造对立的风格遭到了猛烈批判,而“正常总统”奥朗德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缺乏魄力的姿态同样被民意唾弃。希拉克在政治上时常被批评为畏首畏脚、无所作为,然而在总统姿态的问题上,经历了萨科齐与奥朗德的法国民众却难免对希拉克怀念有加。如何维持既维持总统权威又保持亲民形象、如何锐意改革保持魄力又尊重各方维护团结,希拉克的两位继任者只给出了两种失败的尝试。
希拉克主义——同时也是密特朗主义终结的时刻终于在2017年到来。在2017年总统选举的竞选过程中,希拉克的政治继承人朱佩和政治挑战者萨科齐在右翼初选中直接被淘汰,初选胜者菲永(François Fillon,也曾在希拉克任期内担任部长)受到丑闻——仍是老套的虚设职位领公饷,不过在菲永这里主要是为自己的妻子——影响,最终未能进入第二轮。而在左翼,曾在密特朗执政期间担任政府幕僚、仍不时举出密特朗作为标杆的社会党总统奥朗德面对极低的民意支持率,决定放弃参选。而社会党官方候选人阿蒙在第一轮中仅得票6.4%,排在第五位。希拉克在2002年的对手国民阵线再度进入第二轮,让-玛丽•勒庞的女儿马琳娜•勒庞(Marine Le Pen)最终以34.9%的第二轮得票率大幅落败,被挡在爱丽舍宫之外。一个名叫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39岁年轻人带着他创立才一年的政治运动“前进!”(En Marche !),一举赢得总统选举并拿下议会多数,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登上了共和国权力最高峰。
马克龙带来的旋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清算了希拉克主义与密特朗主义的政治遗产:左翼社会党在2017年总统选举后一蹶不振,至今并无起色;而右翼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也仅得票8.5%,沦为第四大党。在2017年后的“新世界”中,不仅曾在希拉克麾下的政坛旧将纷纷退场,希拉克曾力主的“共和阵线”也已经失去意义:传统的左右分野在政治现实中已经让步于马克龙与勒庞的“世界主义-本土主义”对立,极右翼晋升为法国政坛全新两极中的一极,地位似乎已难以撼动。以明显优势赢得总统选举的马克龙在上任一年半后,遭遇了规模空前的“黄马甲”运动(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一部分法国民众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不断上街表达不满,从抗议燃油税上涨发展为对财税乃至政治制度的全面抗争。马克龙被迫放下“朱庇特总统”(« président jupitérien »)高高在上的身段,组织全国大讨论并亲自在各地直接参与辩论。他的改革日程也因为“黄马甲”运动和涉及其亲信的一系列丑闻而受阻。在迎面而来的法国政治与社会现实面前,带着改革者光环的马克龙终于也要直面历任共和国总统都必须面对的种种困境,“新世界”的构筑仍然任重道远。
作为“旧世界”中最后一位广受尊敬的总统,希拉克拥有“旧世界”政客的标准履历和他们所有优缺点,也需要为这个世界的衰落与退场负同等的责任。如今,希拉克连同他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而当马克龙哀悼这位“旧世界”的巨人时,共和国的前景仍不明晰。
编辑:杜卿

播客:https://euroscope.fireside.fm/subscribe
微信公号:搜索“欧罗万象EuroScope”
群邮箱:euroaffairs2017@gmail.com

关于欧洲政治的一切,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本文由地球日报转码显示,查看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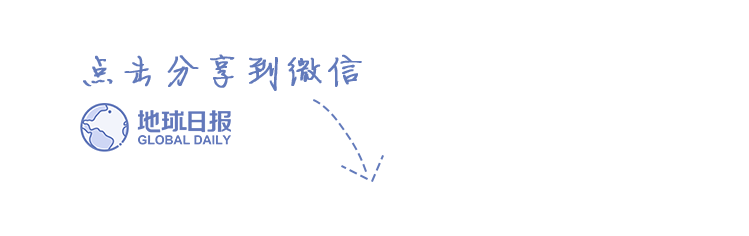

TOP COMMENT
热门评论
没有更多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