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电影崛起,有某些共性
来源:看世界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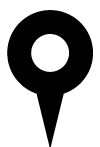
电影《驾驶我的车》剧照

在电影爱好者间,近来最热的话题莫过于《驾驶我的车》。在刚落幕的第74届戛纳电影节上,它拿下场刊最高分,并斩获最佳编剧奖。这部电影改编自村上春树短篇小说集,讲述舞台剧演员兼导演家福悠介在妻子去世后,内心的孤独和失落。近年来,以日韩电影为代表的亚洲电影,正在欧洲电影节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70年前,当欧洲影坛因为黑泽明等不世出的天才电影人,而向东看去时,日本民众最钟爱、日本导演最擅长拍摄的,仍是最具民族特色,宣扬忠义、勇敢、隐忍精神的武士电影。韩国电影在欧洲的“发迹”也有些相似。最早在欧洲顶级电影节上捧回奖杯的韩国电影,其故事背景也是遥远的朝鲜李朝。但随着日韩电影工业发展日趋成熟,其每年都能稳定出产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类型片,无论在制作还是宣发上都有了长足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声量也愈加壮大。西方影评人也不再将日韩电影单纯视为独特的东方符号,转而欣赏其带有国情特色的独特叙事。

《驾驶我的车》在第74届戛纳电影节获最佳编剧奖。图为导演滨口龙介高举奖杯

解放日式审美
日韩两国中,最先受到欧洲关注的是日本。1951年,黑泽明带着《罗生门》在威尼斯斩获了一尊金狮。以挑剔著称的欧洲影评人,自此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此后一段时间里,日本电影在欧洲各大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每年都会给欧洲带去惊喜。

电影《罗生门》剧照
考察这一时期日本电影在欧洲的表现,大部分作品都充满浓郁的东方色彩。如《地狱门》,故事以日本源平合战(1180—1185年)为背景,讲述了出身低微的武士盛远觊觎重臣的妻子引发的爱恨纠葛。
值得一提的是,《地狱门》是日本影史上,首部运用日本国产的伊斯曼彩色胶片摄制的作品。影片工整细腻,堪称教科书式的构图,与当时相对罕见的彩色交相辉映:雍容雅致的服装造型、空灵的自然风光、杀伐决绝的武士、缠绵婉转的东方乐器……很好地在大银幕上,为观众展现了如浮世绘般华美的画面,让观众感受到最纯粹的东方韵味。

电影《地狱门》剧照
当然,日本电影在50年代的爆发并非偶然,除了在二战前就已与欧洲电影有广泛的交流外,也与当时宽松的电影管制有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盟军司令部下属的民间情报教育局负责监管日本电影。
该机构认为,彼时的日本电影过度鼓吹军国主义思想,遂以法令的形式,限定日本电影拍摄题材,而被认为宣扬暴力和愚忠的武士题材电影出路变窄,一些带有民主启蒙色彩、重视个体情感的电影随之涌现,这也为解禁后日本电影的快速发展积累着养分。
这样的限制并未持续太久。1951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日本正式恢复国家主权,盟军对日本电影的监管就此终结,被压抑6年的武士电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用心棒》剧照
除了画面的东方韵味外,日式的故事审美同样给予西方影评人极大的新鲜感和震撼。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有着独特的道德规范,集中体现在“忠”“孝”“情义”上,这也导致了日本故事中很少见到大团圆结局。
这样的情节设计,对看惯了善恶有报模式的欧美观众而言,无疑是新鲜和极富思辨的。这也成为了日本电影在当时受到欧美评论家青睐的另一重要理由。

凸显命运的武士电影
1953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播放第一批电视节目。自此,电视在日本娱乐行业的占比逐渐上升,这对日本电影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电影观众逐渐减少,制片厂辉煌不再,场面宏大、制作精良的大制作变得十分稀缺,日本电影不得不从重画面转向重表达。
在这个过程中,黑泽明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人物。日本媒体称赞道:“在黑泽明之前,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富士山、艺伎和樱花,从他开始,才是黑泽明、索尼和本田。”

黑泽明
武士是黑泽明一生中最热爱的题材。依托武士影片这把“刀”,他将日本武士传统劈开揉碎;他对武士的解构,也影响了后世无数的年轻导演。
早在1950年,黑泽明执导《罗生门》时,他便开始了对传统武士形象的颠覆。在他的镜头下,武士不再是代表秩序和正义的高大全形象,反而更像是空有武士名衔的普通男子。
在1954年的《七武士》中,黑泽明更是延续了此前思路,塑造了7位性格和遭遇各异的武士。在黑泽明的故事里,武士卸去了武士道赋予其的自尊与自傲,变成了鲜活的个人,人物形象入木三分。

电影《七武士》剧照
自此之后,优秀的武士电影不再是东方乱世中各种传奇经历的描述,而开始关注纷繁复杂社会中的个体命运。这与西方推崇的价值观无疑高度一致。
这种思考在《影武者》中达到了顶峰。耄耋之年的黑泽明,套用战国时代大名武田信玄死后三年秘不发丧的传说,讲述了身份低贱的窃贼只因容貌与信玄相似,便被当成信玄替身的故事。

电影《影武者》剧照
作为小人物的影武者,并不甘心只是扮演他人,但传统道德中的报恩与忠诚,很快将其裹挟。他身上背负的武田家历史使命,也最终将自己吞噬,以至于在身份被揭穿后,原本有逃命机会的他,却因为无法适应原有身份,只能选择战死。这样一部个体悲剧与家族悲剧相互映衬的电影,帮助黑泽明拿下了戛纳电影节的最高奖。
具备同样特质的还有今村昌平。他的《楢山节考》讲述了百年前日本的残酷习俗,因为贫困,老人到了70岁后,就得由孩子背到楢山上,独自待死。其内核依然反传统。

电影《楢山节考》剧照
在《楢山节考》里,今村昌平用极尽平实的镜头语言,残酷而悲悯地展现了人性在生存面前的不堪一击,展现了独特的东方生死观。这部电影因此获得了1983年第36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

类型片的胜利
如日本电影般,从展示民族性到追求普世性的还有韩国电影。韩国电影工业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80年代,资本才大规模进入电影市场。
1987年,以朝鲜李朝为背景的电影《借种》,让韩国电影在欧洲顶级电影节上崭露头角。2000年和2002年,韩国电影教父林泽权凭借《春香传》和《醉画仙》,两度入围戛纳金棕榈奖评选—光听名字便能感受其浓浓的古典韵味。

电影《醉画仙》剧照
然而,这两部电影更像是韩国影人在欧洲留下的惊鸿一瞥。从2004年起,韩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展现出极致和凌厉的一面。
朴赞郁2004年获得金棕榈奖的《老男孩》,展现的是韩国人最为钟情的暴力复仇美学;李沧东的《绿洲》讲述的是顶罪者和重度脑麻痹患者间的爱情;金基德《空房间》和《撒玛利亚女孩》的主角都是社会边缘人士,其内核满是喷薄而出的欲望。极端环境下的极端情感,成为了韩国电影的新标签。

电影《老男孩》剧照
极致的设定,让韩国电影满足观众“猎奇”心理,刺激票房,最终反哺电影行业。而韩国电影工业的成熟,则让导演可以在各种类型片中游走,尝试更多不同的可能。
以2019年拿下第72届戛纳金棕榈奖的奉俊昊为例。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寄生虫》是我之前电影的延续,都是类型电影,我一直是个拍类型片的导演。”
从影21年,奉俊昊拍摄的电影类型跨度很大,怪兽片《汉江怪物》,科幻片《雪国列车》,悬疑片《杀人回忆》。充足的人才储备,让导演切换各类型游刃有余,从而能在类型片中,表达自己的思考。
如在《汉江怪物》中,奉俊昊一反怪物电影套路,让怪物早早就露出了真身。最后击败怪物的,也不是传统套路中的大英雄,而是不起眼的小人物。
这样的“反类型”与隐喻,贯穿了奉俊昊全部作品,这也让他最终获得了欧洲顶级电影节的垂青。

奉俊昊
在《寄生虫》中,奉俊昊树立了夸张的人物对立关系,展现的是其对如今韩国严重贫富分化的深刻社会关怀。将社会议题融入本土类型片中,这成为了韩国电影在欧洲顶级电影节上的最新标签。
从初登欧陆时的古典与青涩,到如今成为欧洲顶级电影节的常客,日韩电影的成功是其孜孜不倦探索的成果,也是其电影工业体系化的胜利。正如一位影评人所言,对工业生态本身的重视,对于电影技艺的尊重和体悟,以及对市场并非一味迎合,是日韩电影蓬勃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者 |怜青
编辑 | 吴阳煜 wyy@nfcmag.com
排版 | 李鱼





TOP COMMENT
热门评论
没有更多评论了